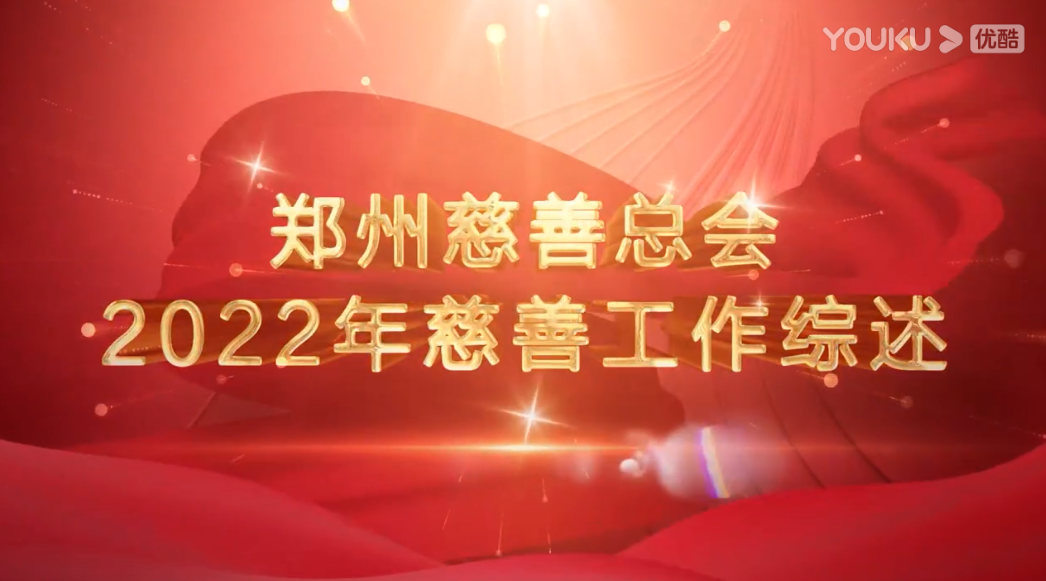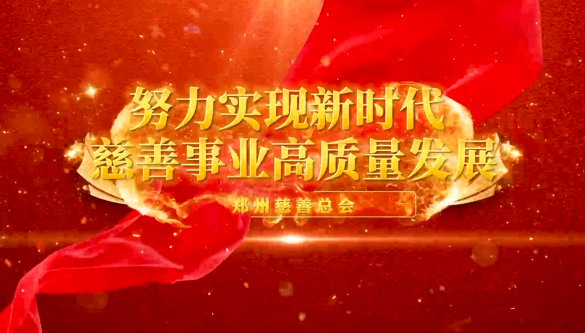數(shù)家防艾NGO有“身份“ NGO新生存規(guī)則或已形成
據(jù)了解,今年8月底,全球抗擊艾滋病、結(jié)核病和瘧疾基金(簡稱全球基金)解凍數(shù)億美元對華援助資金。今年5月份,全球基金曾凍結(jié)上億美元用于抗艾的對華援助資金。
盡管資金被解凍,但據(jù)了解,三個項目的援助資金都比原計劃有所減少,削減幅度或?qū)⒊^五成。資金的消減是否會給本土的草根NGO帶來影響備受人們關注。
小組"被成立"
今年4月份,國內(nèi)第一家由感染人群組成的防艾社團,昆明市西山區(qū)健康關愛促進會(下簡稱"促進會")低調(diào)注冊。
2007年初,促進會副秘書長普建國和幾個同伴作為防艾目標人群的受益者參與到了西山區(qū)紅十字會陽光家園IDU(注射吸毒人群)項目中,他們主要的工作是針對吸毒者的針具交換進行干預。
普建國最初僅是懷著一顆感恩的心參加了這個干預小組的活動,在幾次活動后,普建國結(jié)識了之后成立的促進會的其他幾位核心成員,也鎖定了一批他所服務的目標人群。后幾經(jīng)大浪淘沙,這些核心人員依然堅守,目標人群也在不斷增長,普建國說:"這是小組得以注冊的基礎。"
2007年底,一個屬于昆明市紅十字會的艾滋病綜合干預項目被分配到昆明市各個區(qū)的疾控中心,普建國并未意識到這是一個機會。
成立小組是普建國和同伴們參加IDU項目時就有過的想法,但這一想法只是一閃而過。西山區(qū)疾控中心艾滋病防疫科科長寧躍猛在去年年底前某一天找到了普建國,兩人在IDU項目時就曾相識,這一次兩人就許多問題做了深入交流,其中一個內(nèi)容正是"普建國該成立一個相關工作小組了。"
寧躍猛對普建國觀察已久,更重要的是西山區(qū)疾控中心需要一個社會組織來協(xié)助自己完成上面分配的任務。在寧躍猛的倡導和幫助下,普建國和同伴們組建了"螢火蟲小組",工作的內(nèi)容和之前的IDU項目差不多,這個小組便是促進會的前身。
寧躍猛對《公益時報》記者說:"作為一個敏感領域,防艾抗艾小組自發(fā)成立的很少,在衛(wèi)生部門的引導和幫助下成立占了絕大部分。"
"被獲得"合法身份
"螢火蟲小組"成立之后,先后執(zhí)行過多個項目。普建國和這個小組在執(zhí)行這些項目的過程中自身能力也得到提升,與西山區(qū)疾控中心形成良性互動,"我們更多的是管理感染人群信息和給予他們技術(shù)支持,很多具體的工作交給他們做更合適",寧躍猛說。這些良性互動正在促進著促進會的注冊。
對于正式注冊的事情,普建國很猶豫了,"缺乏的東西太多,即便注冊成功,也可能最終因年檢無法通過而關閉,何況我們對注冊的程序、要準備的材料一無所知。"普建國對自身和團隊能力的不足認識很清楚。
但對于注冊的渴望依然強烈。薪水和社會福利無法得到保障,成為"螢火蟲小組"核心人員流動頻繁的一個根本原因。"只有合法的身份,才有獨立的賬戶,很多項目才可以申請,這才是組織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根本",寧躍猛在接觸過這么多小組后深有感觸。
現(xiàn)行法規(guī)要求,一個組織要申請登記注冊,必須有相關的業(yè)務主管單位的批準,同時該單位必須為政府職能部門或法律法規(guī)所許可的特定機構(gòu)。對于民間自發(fā)的草根NGO,尤其在某些敏感領域來說,得到相關業(yè)務主管單位的批準并申請獲得登記管理機關的登記注冊,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西山區(qū)疾控中心對于"螢火蟲小組"在干預工作上出色表現(xiàn)是看在眼里,給予一定肯定是必然的,這個最好的肯定是幫助他們正式注冊成組織。除了這個原因,寧躍猛還感覺到一個趨勢,"整個境外資金的流入在減少的。一份數(shù)據(jù)也在表明,自中國GDP超過德國后,境外投入中國NGO的資金在正遞減。
疾控中心完全主導了此次注冊。首先疾控中心將西山區(qū)防艾抗艾資源做了一個整合,將西山區(qū)的幾個不同內(nèi)容的小組整合在促進會旗下,同時疾控中心領導擔任了促進會會長,寧躍猛成了促進會的秘書長,疾控中心的財務也兼任著促進會的財務,疾控中心在資源上、技術(shù)指導上都給予了促進會最大的方便。
整個注冊流程都是疾控中心在跑,而且很快促進會的注冊申請就被批下來。普建國至今還不是很清楚促進會究竟有沒有掛靠。
網(wǎng)絡"被收編"
普建國和"螢火蟲小組"無疑是幸運的,羅志也有這樣的幸運,而且幸運中還帶有一點"狡猾".
昆明云迪行為與健康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云迪研究中心)是2002年成立的一家以調(diào)查、研究艾滋病感染人群行為為主社會組織,最初是由昆明醫(yī)學院幾位老教授倡議組建注冊而成。
羅志是2005年進入到云迪研究中心,當時的身份還是志愿者。作為一位前吸毒人員,在被強制戒毒后,對于毒品的危害產(chǎn)生深刻的認識,因為在戒毒期間有接觸過許多義工,戒毒成功后羅志也積極投身到了這個領域。
羅志用了4年的時間得到了云迪研究中心教授們的認可,他自己也成為了一名資歷深厚的同伴培訓師,曾擔任國際機構(gòu)IDU戒毒所項目的協(xié)調(diào)員,培訓員,為全球基金項目和中澳項目培訓過外展人員和戒毒所同伴教員2000多名。從2008年開始,羅志開始擔任云迪研究中心的管理工作。
在羅志做培訓師的那幾年,他也認識各式各樣的草根組織,但這些草根組織發(fā)展都不是很好,在開展一段時間工作后因為各種原因都各自解散。羅志認為各地草根組織有必要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互相學習各自的經(jīng)驗,在優(yōu)勝劣汰的草根組織競爭中得到更好的發(fā)展。
在他的倡議下,2008年在云迪研究中心成立了云迪-云南減少傷害網(wǎng)絡(下稱云迪減少傷害網(wǎng)絡)組織。云南省23個市縣和廣西南寧市共25個草根組織加入網(wǎng)絡,整個網(wǎng)絡組織共有成員約280余人網(wǎng)絡組織成員,固定管理辦公室就設在了昆明的云迪研究中心。
云迪減少傷害網(wǎng)絡在云南草根組織的名頭很大,它聯(lián)合發(fā)出的一個倡導改變了國家禁毒政策方面的一個條例,這在任何一個領域都是很難,更不用說在這么一個敏感的領域。
云迪減少傷害網(wǎng)絡在云南省10個縣、廣西3個9縣市開展了吸毒人員動態(tài)管控系統(tǒng)退出機制研究,該研究共調(diào)查了200名既往吸毒人員對吸毒人員動態(tài)管控系統(tǒng)的態(tài)度、影響,透析吸毒人員對動態(tài)管理系統(tǒng)的真實想法及評價等,最后由云南省多家組織發(fā)起聯(lián)合倡導,請云南省艾滋病領域國家級專家李建華教授到國家禁毒辦遞交聯(lián)合倡導建議書,得到了國家的認同,并于2011年成功將全國6.8萬既往吸毒人員從該系統(tǒng)中屏蔽。
按理說,這么一個有實力、有影響的草根組織是具備了注冊的實力,但羅志對此還是采取了極其保守的態(tài)度,"無論從自身還是外部環(huán)境,注冊都離NGO還有一段距離",羅志培訓師身份的一個工作是給云南各個草根組織作能力建設培訓,"云南絕大部分草根組織都沒有達到注冊的能力,他們對NGO的管理幾乎空缺".
羅志也沒想過要給云迪減少傷害網(wǎng)絡注冊,但他很巧妙地利用了云迪研究中心的"招牌".羅志自從參與云迪研究中心的管理工作和組建云迪減少傷害網(wǎng)絡以來,兩部分的工作已很難分開,為此他找到當初創(chuàng)建云迪研究中心,如今已閑賦在家的幾位老教授,他們同意將云迪減少傷害網(wǎng)絡用云迪研究中心的牌子和賬戶,由此云迪減少傷害網(wǎng)絡正式被"收編".
這無疑是幸運的,羅志憑借自己的關系將云迪減少傷害網(wǎng)絡送入了合法的范疇,整個網(wǎng)絡也有了更廣闊的發(fā)展空間。
新游戲規(guī)則形成?
在本土NGO通過各種途徑獲得"身份"的同時,全球基金項目資金的減少是否會對本土的NGO帶來影響?普建國接受一家媒體時曾說過這么一段話,"據(jù)估計,云南地區(qū)受資金凍結(jié)影響的防艾草根NGO大概在160多家,絕大部分草根小組處于停工狀態(tài),我們已有6個月沒發(fā)一分工資了。"但他卻認為可能是記者采訪時沒溝通好,他向《公益時報》記者解釋:"'全球基金'確實給云南的NGO帶來很大影響,但這種影響只是對那種太過依賴'全球基金'的草根而言。"
"以我們'螢火蟲小組'為例,我們從'全球基金'申請過的資金只有34000元,這筆資金在'全球基金'的項目中只占到中等,但所能開展的活動也是有限的,'全球基金'是依據(jù)你小組的目標人群數(shù)來劃定資金",普建國進一步解釋道,"至于我們6個月沒發(fā)工資,與'全球基金'也并無關系,只是我們組織剛注冊,許多事情還沒辦好,暫時沒發(fā)工資而已".
一位前"全球基金"項目主管也認為,"全球基金"對國內(nèi)NGO的影響并沒有想象中那么深,國外有很多基金會投入的資金比"全球基金"多很多,其根源還是在于政府如何有效地管理這些草根NGO.
有專家認為國內(nèi)NGO生存在某些開放地區(qū)已有了廣闊的空間,一個新的游戲規(guī)則正在形成。防艾的草根NGO應該去試探一下國家相關部門的底線,以便自身在將來競爭激烈的公益組織中搶占先機。